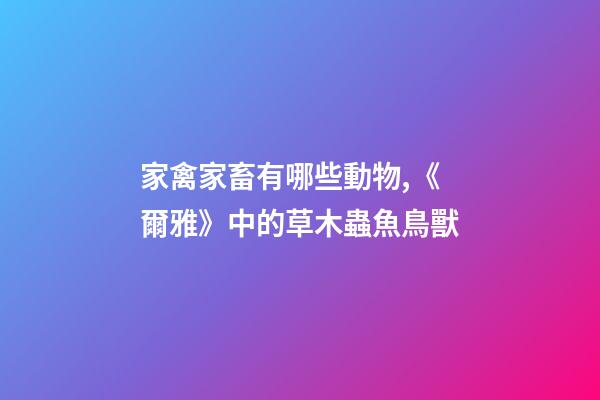
來源頭條作者:中華書局在《爾雅》一書中,最妙的文字應(yīng)屬自《釋草第十三》以下的七篇(《釋草》《釋木》《釋蟲》《釋魚》《釋鳥》《釋獸》《釋畜》)。這七篇是對于草木蟲魚鳥獸的解釋,是先秦時代古人對于自然萬物的觀察的總結(jié)。可以說,這七篇組成了一份來自二千年前的“博物指南”。《爾雅新注》顧名思義,所謂《釋草》《釋木》《釋蟲》《釋魚》《釋鳥》《釋獸》《釋畜》,也即對在古人日常生活中所見到的草木蟲魚鳥獸與家畜的解釋。草,指今天所見的草本植物;木,指今天所見的木本植物。蟲,古代可以指一切動物,不過在《爾雅·釋蟲》里的蟲,主要說的是今天的昆蟲。魚,在這里指水生動物。包括了一些軟體動物、兩棲動物和爬行動物,蛇類也算入。鳥,在《爾雅》中指能飛行的動物,除了今天的鳥類之外(雞類除外),連蝙蝠、鼯鼠之類也算入其中。獸,在《爾雅》中包含今天的鹿類、豕類、鼠類以及其他虎豹熊羆等。畜,在《爾雅》中指人豢養(yǎng)的馬類、牛類、羊類、犬類、雞類等家禽家畜。以上七篇所解釋的動植物,其總數(shù)近六百種。在《釋草》一篇中,不僅涉及了蒮(yù)、茖(gé)、葝(qíng)、蒚(lì)等可以食用的野草,而且還有菉(lù)、蒤(tú)等可以用作染料的原材料。最值得注意的是,出現(xiàn)在《詩經(jīng)》里的草類,基本上被《爾雅》所記錄。例如《召南·采蘩》“于以采蘩,于沼于沚”之“蘩”,《鄭風(fēng)·東門之墠》:“東門之墠,茹藘在阪”之“茹藘”,《豳風(fēng)·東山》“果臝之實,亦施于宇”之“果臝”,《小雅·白華》“白華菅兮,白茅束兮”之“白華”,《小雅·我行其野》“我行其野,言采其葍”之“葍”,《大雅·緜》“緜緜瓜瓞”之“瓞”等等。《詩經(jīng)注析》(中華國學(xué)文庫)同樣,在《釋木》等其他六篇中,除了一些古時人們常見常知的,也有出現(xiàn)于《詩經(jīng)》里的樹木,例如《杕杜》“有杕之杜”之“杕”。正因為《爾雅》與《詩經(jīng)》聯(lián)系緊密,故而早至清代王樹楠就已經(jīng)開始系統(tǒng)研究二書的關(guān)系,并撰成《爾雅說詩》一書。有趣的是,《爾雅》中不僅記載了名實相異的物種,還記載了同一物種下的品種之別。例如在《釋畜》一篇中,《爾雅》詳細(xì)記載了各種不同的馬。如以四足白色與否論之,即有如下劃分:馬膝以上全白的馬,稱為“馵”(zhù);馬膝以下全白的馬,稱為“驓”(céng);四馬蹄全白,稱為“騚”(qián);前二足全白的馬,稱為“騱”(xí);后二足全白的馬,稱為“翑”(qú);四足之中只有前右足白色的馬,稱為“啟”;只有前左足白色的馬,稱為“踦”;只有后右足白色的馬,稱為“驤”等等。《爾雅 附音序、筆畫索引》甚至,連馬身上的旋毛所在不同,也有不同的稱呼。胸前有旋毛者,稱為“宜乘”;旋毛在馬肘之后者,稱為“減陽”;旋毛在脅部者,稱為“茀(fú)方”;旋毛在馬背之上這,稱為“闕廣”。自然,馬的毛色不同,稱呼也有相別。如毛色赤白相間者,稱為“駁”;黃白相間者,稱為“騜”(huáng);毛色為赤色,而脊背為黃色者,稱為“騝”(qián);毛色為赤色,而脊背為黑色者,稱為“騽”(xí);毛色為鐵青色者,稱為“駽”(xuān);毛色有鐵青色的鱗狀紋的馬,稱為“驒”(tuó);毛色為鐵青色的長鬃馬,稱為“騥”(róu);黑白相間而有雜色的,稱為“駂”(bǎo);黃白相間而有雜色的,稱為“駓”(pī);紅白相間而有雜色的,稱為“騢”(xiá);淺黑、白相間而有雜色的,稱為“駰”(yīn);深青、白相間而有雜色的,稱為“騅”,楚霸王項羽所乘之馬,就是這種。[清]郎世寧《郊原牧馬圖》,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《爾雅·釋畜》中解釋馬、牛、羊、犬、雞五類,而馬類占據(jù)該篇近一半篇幅。可見在先秦時代,馬在當(dāng)時人的生活里有著非常重要的比重。不過,細(xì)心的人可能已經(jīng)發(fā)現(xiàn),《釋畜》一篇中是沒有“豕類”的,也就是沒有豬這一類的。這一類在《爾雅》中被放入了《釋獸》一篇中。從行文措辭上看,馬類、牛類、羊類和豕類的寫作結(jié)構(gòu)是相似的,放在《釋獸》一篇里,頗令人懷疑這是不是錯簡。當(dāng)然,并非《爾雅》記載的所有動植物今日都能看見。如《釋獸》之“貀(nà),無前足。”《釋鳥》之“鳥鼠同穴,其鳥為鵌(tú),其鼠為鼵(tū)。”《釋魚》之“鱉三足,能。龜三足,賁。”《釋蟲》之“蝎(hé),桑蠹。密肌,繼英。”《釋木》之“休,無實李。駁,赤李。”上述這些或是文字太過簡短,或是太過怪誕不經(jīng),又或是太泛泛而談,以致于古人所言僅能留在紙面,無法以現(xiàn)實印證。這也同時說明,《爾雅》的《釋草》等七篇,其實還是倚賴整飭各種古文獻(xiàn)的記載(例如《釋鳥》之“鳥鼠同穴”,就見于《山海經(jīng)》),加之以補入后來所見者而成的。《山海經(jīng)詳注(插圖本)》(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)《爾雅·釋草》等七篇既記載了到今天現(xiàn)實里還有的動植物,又記載了存在于古文獻(xiàn)里的、帶著神話色彩的動植物,信息量極其豐富,但其措辭卻極其簡短。因此,對今天的人來說,要讀懂這個書有很有些難度。不過,《爾雅》作為“十三經(jīng)”中“謎團”最多的儒家經(jīng)典,到現(xiàn)在也很吸引人為它作一番疏解的工作。而對于《爾雅·釋草》等七篇的詳細(xì)考釋,自然是題中應(yīng)有之義。在王建莉老師的《爾雅新注》一書中,《釋草》等七篇的條目詮解,很是下了一番苦功。因此,對于今天的想要閱讀《釋草》等七篇的人來說,《爾雅新注》就是一本可常備于案頭的參考書。【贈箋紙】《爾雅新注》(精)(贈注者王建莉簽名箋紙一枚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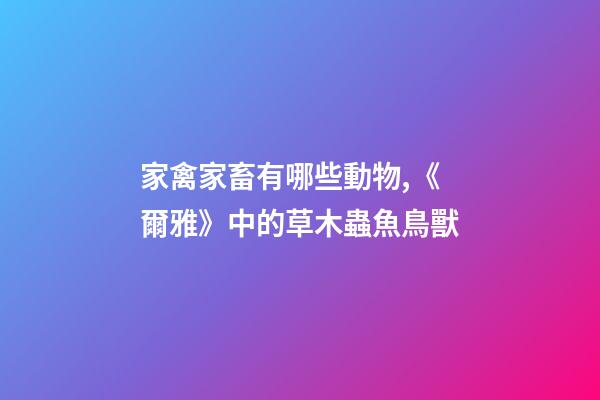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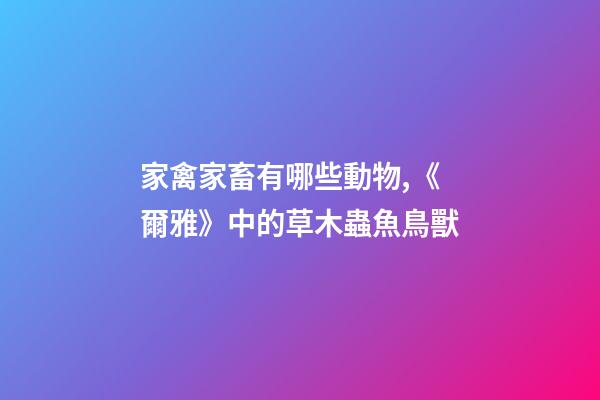

暫時沒有評論,來搶沙發(fā)吧~